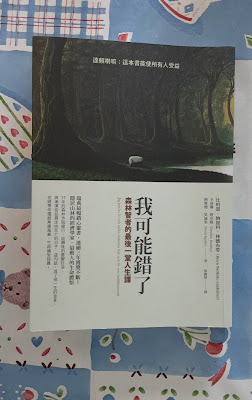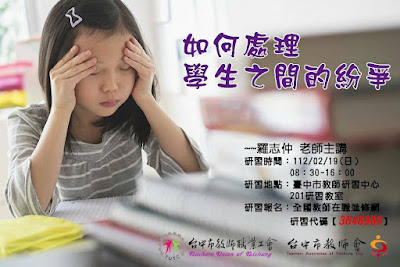工作很累,想辭職不做,怎麼辦?
朋友問我,她工作得很累,想辭職不做,怎麼辦? 我問她,是希望我提供建議,還是與她對話? 她問,這兩者有何不同? 我說,提供建議不一定有幫助,因為那只是我個人的觀點與生命經驗。對話則可幫助她進入內在,釐清自我,進而做出最適合她的決定。 她想了想,有些遲疑:「如果我不熟悉冰山理論,也可以對話嗎?」 我說,當然可以,熟悉冰山理論是我的責任,不是她的。但如果她有興趣,我可以一邊對話,一邊說明我為何那樣對話。 朋友點點頭,表示願意。 我從「感受」切入,問她此刻感覺。 她說,是哀傷。 「哀傷什麼?」 「哀傷工作永遠做不完,每天都要加班。」 「妳希望有什麼不一樣嗎?」我轉而走她的「期待」。 「如果每週只加班一、兩次,我可以接受。我希望能有時間做自己的事,過自己的生活。」 「聽起來,妳渴望多一點自由,是嗎?」我連結她的「渴望」。 「是呀。」她嘆了一口氣。 「是什麼阻礙妳得到自由呢?」 她想了一會兒,苦笑道:「責任感。」 「妳的苦笑是什麼?」 「因為我們家人都很有責任感。」 「如果妳在工作上少一點責任感,會發生什麼事嗎?」我挑戰她固守已久的「觀點」。 她想了一會兒:「其實不會。」 「如果少一點責任感,多一點自由,妳可以接受嗎?」 她深深嘆了一口氣:「可以,因為我快扛不住了。」 「那麼,妳覺得,在妳目前的能力範圍內,妳能為自己做些什麼改變呢?」 她開始列舉幾種她可以做得到的方法,包括「每次最多只加班一小時」,而我也再三跟她確認:「妳確定這樣OK嗎?」「這是妳可以接受的嗎?」「這是妳做得到,也願意嘗試的嗎?」 最後,我向她核對此刻的「感受」:「妳現在還是覺得哀傷嗎?」 「是呀,但是好多了。」 「如果10分是滿分,1分是最低分,來找我前,妳的哀傷是幾分?現在又是幾分?」 「本來超過10分,都滿出來了,現在還有7分。」 「如果哀傷無法完全消失,幾分是妳可以接受的?」 「3分吧。」 「如果用妳剛剛為自己想到的方法去工作,妳覺得妳的哀傷有可能從7繼續減少嗎?」 「應該可以。」她的眼睛亮了起來。 「我感覺妳現在的狀態,似乎和剛剛一開始的時候不太一樣,有嗎?」 「有!」 「有什麼不一樣?」 「現在比較篤定、安心了。」 「喔?篤定、安心是怎麼來的?」我停頓了兩秒。「或者說,在剛剛的對話中,是從什麼地方開始讓妳覺得比較篤定、安心的?」 「當你問我: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改變?應該是從那個時候開始。」 我笑說...
.png)